关于“富都”和电影涉及的非法劳工,王礼霖把视角沉到这个环境中,通过一场看似荒唐的冲突,侧面刻画了马来西亚在旅游胜地之外的另一面,则更让我大感意外。
也许每个地方在光鲜之外,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暗面。
有些人对《富都青年》的观感不是很好,最主要的原因是社工佳恩之死。
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两兄弟要对一个一直热心帮助他们的女孩子这么残忍?一个在盛怒之下想要强暴她,另一个则在惊恐之中误杀了她。
然后,这两个人居然只是彼此为对方担心,似乎对佳恩并没有任何愧疚。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导演兼编剧王礼霖一开始就没有把他们往“伟光正”的方向上塑造。他只是很客观地描述马来西亚底层人物最真实的爱恨善恶。
不妨略微回忆一下我们国内关于社会治安的报道和采访,回忆一下在新闻里看到的,以及身边如果遇到的那些精神小伙和精神小妹,而大多数观众可能离这些人的生活很遥远,一辈子都接触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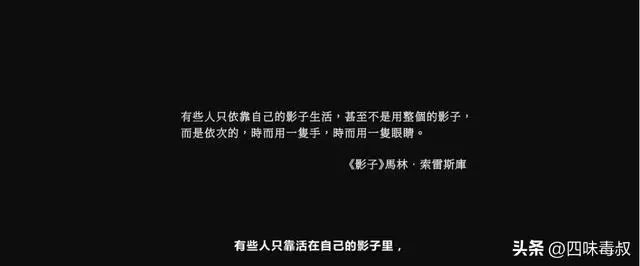
但《富都青年》能让你近距离接触到他(她)们。
至于刻画方式,马来西亚那边显然和中国内地影视剧对底层人物的塑造略有不同,最明显的对比是今年差不多同期上映的《野孩子》——
如果看过的话,基本上就知道不同之处在哪里。
这可能也是《富都青年》在某瓣上评分不高的原因。
但仅凭男一号吴慷仁的演技,我觉得值得一看。

1
兄弟
影片一开始,就聚焦在阿邦(吴慷仁 饰)和阿迪(陈泽耀 饰)这对没有身份证的异父异母的亲兄弟身上。他们是吉隆坡市中心东南部“富都区”的底层人物,富都则是外籍劳工们的集散地,这些人来自东南亚各个国家,统一的特点是没有身份。大家像老鼠一样打着零工,勉强挣扎,活在一处。
马来西亚政府不定期对这里进行清理,搜查、遣返这批非法劳工。“身份证”是他们在这里最渴求的东西,有了它,意味着可以光明正大地打工挣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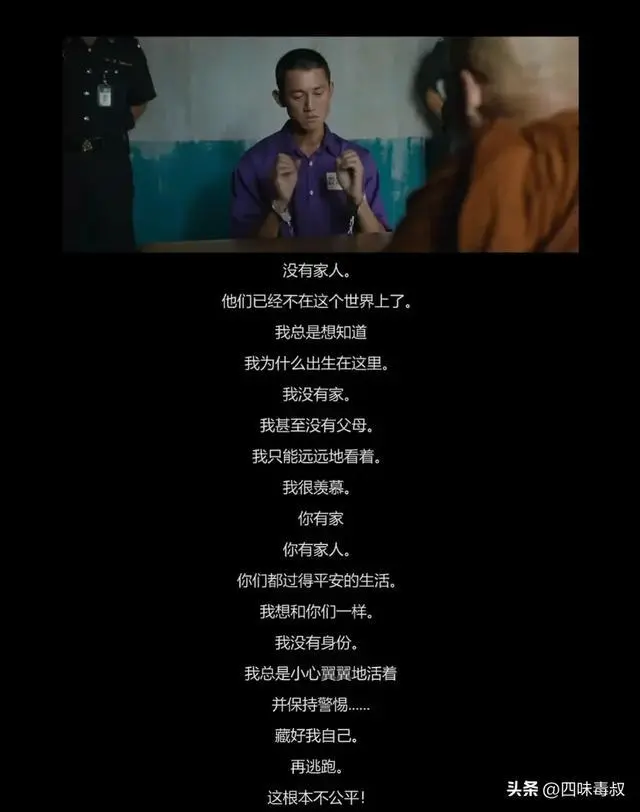
除了政府之外,一些民间组织对他们也多有关注,宗教人士、社区工作人员也会各尽所能,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他们进行有限的帮助。
因此黑白、善恶,就在这个富都之中渐渐弥散。
阿邦和阿迪从来不会花时间思考“我是不是个好人”这样的问题,他们每天唯一思考的是“我怎么活下去?”尤其是阿邦,他常年劳作晒成一身黝黑的皮肤,还时常被临时雇主压榨,人家一句“你争什么?”或干脆什么都不说,阿邦也都认了。
还是因为阿邦是个没有身份的人,每次他和别人聊天、吃饭、逛街、工作,只要看到警察,他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跑。
这种日子他从小到大都习惯了。

阿迪则不同,他性格更加暴躁叛逆,他不屑于打零工,更希望通过一些捷径快速赚到钱。
所以他会跟着黑老大招揽一批同样是非法劳工的外国人,他心思活络,又没什么底线。除了帮人招劳工,还当小白脸陪富婆,每次都能挣到不少钱。
两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攒着钱,每天把当天省下来的钱装进饼干盒里。
吃鸡蛋的时候还会拿着鸡蛋往对方脑袋上磕几下,一边磕一边笑。
那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快乐。
但在富都的世界里,快乐就是个奢侈品。
性格善良的阿邦知道隔壁的缅甸妹对自己有好感,他天生聋哑,需要戴助听器才能和人交流。身体上的缺陷加上身份的卑微,他对未来的日子不抱太大希望。但他依旧渴望爱情。
所以他打扮得很整洁,陪缅甸妹去逛街,还为她买了一条丝巾。
这条丝巾,后来成为他此生唯一的色彩。
另一边,阿迪在一次招揽劳工时遭遇警察突击,惊慌之下他目睹了其他劳工为了不被遣返回国宁愿自杀的惨状。接着他了解到更残酷的真相——
黑老大说每次用完这些劳工,发钱的时候派人打个电话叫警察来,把他们一网打尽,自己就能省下一笔钱。
饶是性情乖张的阿迪也无语了。
他对这个世界的绝望刻在骨子里,但“哥哥”阿邦不这么想,他也辛苦,却依旧保持善意,同样也对对他们好的人感恩。
包括社工佳恩(林宣妤 饰)。
佳恩一直在帮他们寻找解决身份的方法,并隔三差五过来和他们沟通。
阿迪对此不屑一顾,阿邦却感激不已——
这世上还记得他们的人不多,佳恩算一个,MONEY算一个。

2
诉说
吴慷仁后来说他觉得整部电影中,他最喜欢的就是阿邦、阿迪和MONEY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戏。
无论作为演员还是角色,抑或观众,好像这场戏确实是最温柔的一幕。
两兄弟和一个从小看着他们长大的边缘人物边吃饭边嬉闹,似乎日子再苦,也有值得回忆的时刻,然后……
被迅速掩埋在习以为常的苦难中。
缅甸妹走了,阿邦远远看着她,始终没把丝巾送出去。
富婆走了,阿迪为数不多的经济来源断了。
社工佳恩找到他们,对阿邦说阿迪的亲生父亲找到了,可以给他办身份证。
阿邦很开心,阿迪很愤怒。
他想象不到什么人会任由自己的孩子过着二十来年的非人日子。他对世界已经不抱希望。可热情善良的佳恩不懂他的心思,依旧带着资料追着他,在她看来,只要拿到身份证,至少能够让一个人不再是“老鼠”。
恰恰就在那天,恰恰就在阿邦不在的时候,暴虐的阿迪与佳恩吵了起来,他轰佳恩走,佳恩不走。阿迪竟把她按在桌上撕扯她的衣服,挣扎中佳恩给了他一耳光,阿迪反手也抽了她,倒地的佳恩没了动静……
惊慌失措的阿迪找到阿邦,阿邦看着躺在地上流了一摊血的佳恩,他带着阿迪坐上大巴到处逃窜。沿途中阿邦在思索,他下车故意滞留在原地,等着大巴走了,他以为阿迪就此可以离开,其实这时他已经有了顶罪的想法,不料阿迪也下了车,远远地看着他。
两个人似乎生下来就注定了彼此纠葛,也彼此担心。
可阿邦还是去顶罪了——至少阿迪和MONEY一开始都是这么想的。
后来,阿迪从阿邦的记忆中解读了他的痛苦:
阿邦回去过,佳恩也没死。正当阿邦慌张时,他听到屋外有警察走动的声音。他捂住了佳恩的口鼻怕她发出动静,然后……

佳恩真的死了。
监狱里,阿邦恍惚看到了佳恩,佳恩说阿迪的身份证要办好了,她笑得很开心。阿邦却哭得很凄凉。
阿邦对别人“说”:
我很痛苦,像老鼠一样,我想死。
这是全片最扎心的时刻。
3
震撼
阿迪还是去见了自己的父亲,还是办了身份证。
他剃了头发,穿着整齐地见了阿邦。
阿迪对阿邦说自己开始认真工作了,好好做人了。
阿邦笑了。他拿起了鸡蛋,对着阿迪脑门又磕了几下,只是这次磕的时间长了些。
当丝巾飞舞的时候,阿邦也走了。

阿迪看着富都区的那些人,搞不清楚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就要过着老鼠一样的日子。
其实很难形容电影结尾时的感受,因为整个观看过程中,似乎它就在平铺直叙地告诉你底层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它不是白富美帮扶精神小伙,屌丝逆袭登上人生巅峰的爽片。
说它“窒息”倒不至于,但它就是在告诉人们:
很多梦幻经不起推敲。

阿邦比画着的那句“我想死”,也说明没有任何人能搭救他们,他们完全是麻木地活着,然后磨灭掉最后的希望。
因此很难形容那场戏对心理的震撼。
阿迪在阿邦临刑前说:
“下辈子让我当哥哥吧,我保护你。”
让人泪下。
这就是“老鼠”的宿命。

不过吴慷仁凭这部电影拿到了第6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倒也让人折服。
一句台词没有,全靠眼神和肢体把“富都青年”演活了。
关于“富都”和电影涉及的非法劳工,王礼霖把视角沉到这个环境中,通过一场看似荒唐的冲突,侧面刻画了马来西亚在旅游胜地之外的另一面,则更让我大感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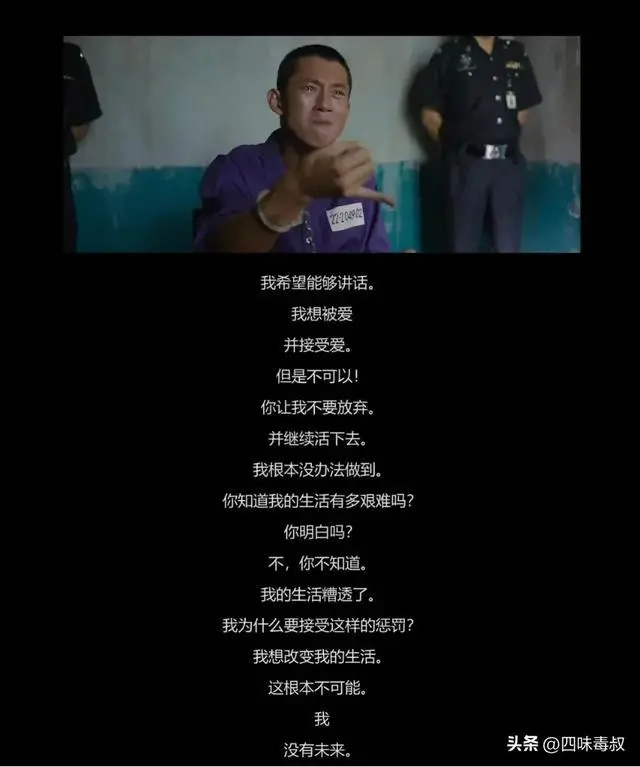
也许每个地方在光鲜之外,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暗面。
又也许一部电影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能让人去看,去感受这种强烈的情绪,如阿邦悲愤的“诉说”。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直面人生的艺术。
